第九部 錫安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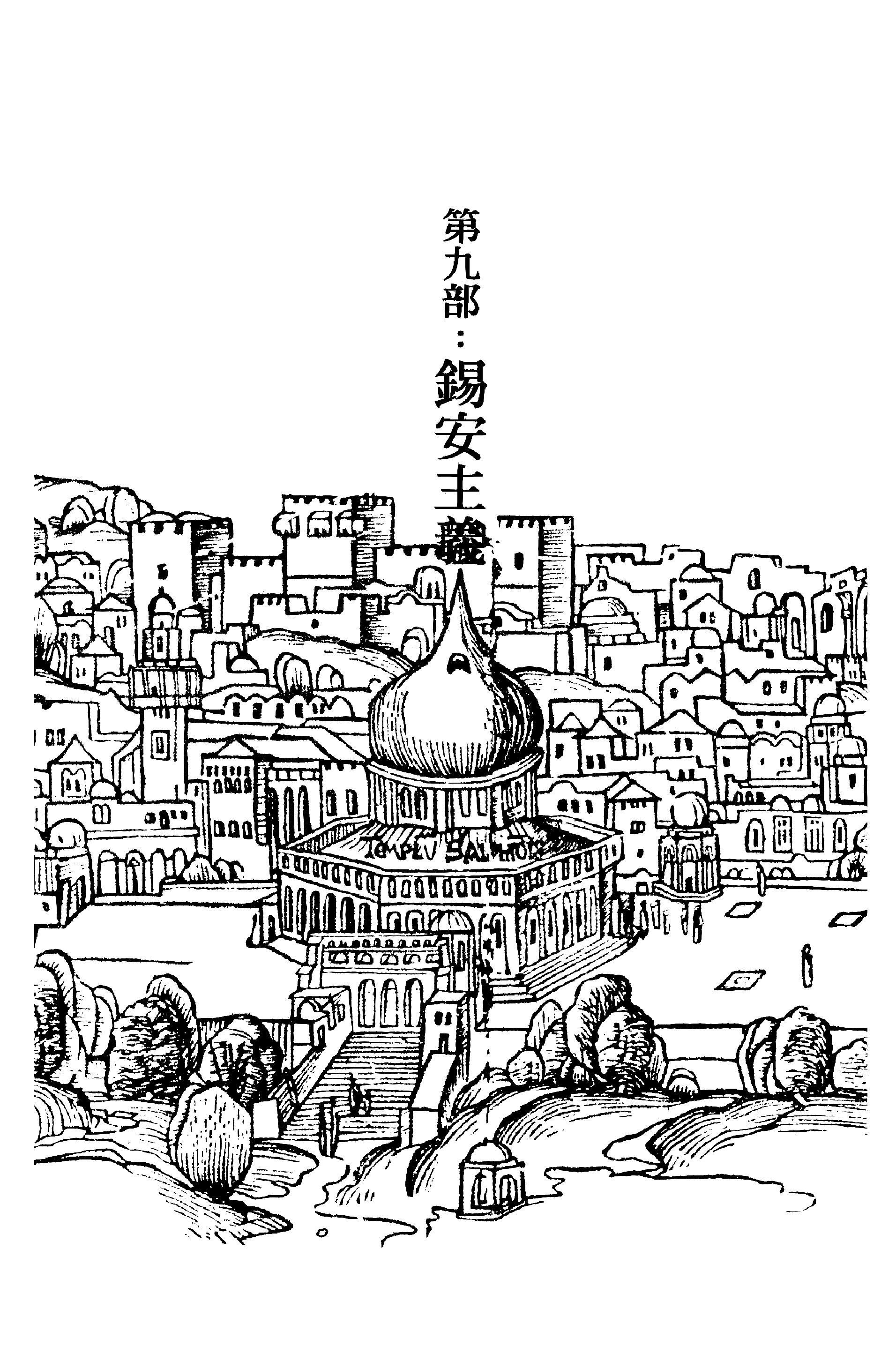
喔,耶路撒冷:拿撒勒可愛的夢想者曾在這裡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然而此地所招致的卻只有怨恨。
——提奧多爾.赫茨爾,《日記》
耶和華憤怒的臉孔凝望著這處炎熱的岩石,此地以神聖為名而進行的謀殺、強|奸與掠奪,遠非其他地方所能比擬。
——庫斯特勒
如果土地也有靈魂,那麼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之地的靈魂。
——戴維.本-古里安,新聞訪談
對全人類而言,沒有任何城市比雅典與耶路撒冷來得重要。
——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六卷〈勝利與悲劇〉
當個耶路撒冷人並不容易。通往愉悅的路上總是滿布荊棘。偉大的人物進到城內也頓覺渺小。教宗、宗主教、國王全得脫下頭上的冠冕。因為這是萬王之王的城市;世間的國王與領主沒 有資格成為它的主人。沒有任何凡人能擁有耶路撒冷。
——約翰.特里爾,〈我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季刊》
非猶太人擔此重任
便須承受以色列的恨,
因為他無法讓
耶路撒冷再度得勝。
——拉德雅德.吉卜林,〈耶路撒冷的負擔〉
42、德皇威廉(西元一八九八~一九○五年)
當赫茨爾等待德皇的召喚,並且探索耶路撒冷這座城市時,皇帝將他自己「特別用心」設計建造的羅曼式塔樓獻給救主教堂(Church of Redeemer)。當威廉造訪聖殿山時,他的考古熱忱使他詢問穆夫提是否能在此地進行挖掘,後者客氣地拒絕他。
親愛的上帝遠比我們清楚,猶太人殺死我們的救世主,因此祂懲罰了猶太人。但我們也不該忘記國際猶太資本擁有廣大且極為危險的力量,如果能讓希伯來人對我們感恩懷德,那麼對德國來說將是極為有利的事。
一八八三年,早在赫茨爾的作品出版之前,第一波為數兩萬五千名的猶太移民抵達了巴勒斯坦——即第一次阿利亞。但耶路撒冷也在一八七○年代與一八八○年代分別吸引了波斯人與葉門人前來。這些移民傾向於集體聚居於一處,組成自己的社區:來自布哈拉(B okhara)的猶太人,包括珠寶商穆薩耶夫家族(Moussaieff family),他們的祖先曾為成吉思汗處理鑽石,此時他們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區。這裡被仔細地規畫為方格狀,區內的宅邸蓋得相當宏偉,而且採用新哥德與新文藝復興的建築樣式,有時還帶有一點摩爾人的風格,這是為了仿傚布哈拉猶太人中亞老家的城市樣貌而做的設計。
德皇與赫茨爾:最後的十字軍與最初的錫安主義者
提奧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是維也納的文學批評家,據說他的「相貌極為出眾,一對杏核眼,加上烏黑濃密的睫毛,散發著憂鬱氣質,側影宛如亞述帝國的皇帝」。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育有三名子女,他是個徹底同化的猶太人,穿著翼領襯衫與大禮服:「他看起來不像猶太人」,也與猶太小鎮裡污穢、鬈髮的猶太人無關。他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律師,不會說希伯來語或意第緒語,他會在家裡立起耶誕樹,而且完全沒想過給兒子行割禮。然而俄國在一八八一年對猶太人進行的屠殺卻令他大為震驚。一八九五年,當維也納選出反猶太煽動者卡爾.魯格(Karl Lueger)擔任市長時,赫茨爾寫道:「猶太人普遍感到絕望。」同年,他前往巴黎採訪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一名無辜的猶太軍官被構陷為德國間謀。他發現在這個已經解放猶太人的國家裡,民眾居然在巴黎高喊「處死猶太人」。赫茨爾因此相信,同化不僅是失敗的,而且還引發更強烈的反猶太主義。他甚至預言,有一天德國會將反猶太主義合法化。
在伊斯坦堡,威廉終於接見了這位錫安主義者,他認為赫茨爾是個「理想主義者,有著貴族般的人品,聰明,與伶俐的雙眼」。德皇表示,他會支持赫茨爾,因為「已經有一些放高利貸的人蠢蠢欲動。如果這些人能移居到巴勒斯坦,將會更有用處。」但赫茨爾反對這樣的誹謗。德皇問赫茨爾,需要他向蘇丹要求些什麼。「一個在德國保護下的特許公司」,赫茨爾回答。德皇於是邀請赫茨爾在耶路撒冷與他見面。
錫安主義本身並不是什麼嶄新的觀念——這個詞在一八九○年就已經出現——但赫茨爾卻為這個古老情感注入了政治觀點與組織內容。猶太人習慣從自己與耶路撒冷的關係來審視自己的存在,這種特質可以上溯到大衛王時代,特別是巴比倫俘囚時期。猶太人朝著耶路撒冷禱告,每年逾和-圖-書越節祝禱彼此「來年在耶路撒冷相聚」,並且在婚禮時打碎一片玻璃,以及讓家中某個角落完全不做裝潢以紀念傾頹的聖殿。他們到耶路撒冷朝聖,希望死後葬在那裡,而且一有時間就在聖殿周圍的城牆禱告。即使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遭受悲慘迫害,他們依然居住在當地,除非他們遭受死亡的禁令。
赫茨爾夢想著,「如果耶路撒冷成為我們的城市,我會清除一切不神聖的事物,拆毀所有藏污納垢的事物」,保存舊城做為遺跡,就像盧爾德或麥加一樣。「我會興建讓空氣不再惡臭的污水道,我要在聖地周圍建造全新的城市。」赫茨爾後來又認為,耶路撒冷應該讓所有人共享:「我們不應該讓耶路撒冷成為某個國家的領土,它不屬於任何人所有,卻又屬於所有人所有,聖地應該由所有信徒共有。」
敖德薩醫師平斯克爾(Leo Pinsker)在作品《自力解放》(Auto-Emancipation )中寫道(與赫茨爾寫作時間大致相同):「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國家。」他激勵俄國猶太人展開新的運動,組成「愛錫安者」,前往巴勒斯坦進行屯墾。即使這些人是世俗人士,年輕的信仰者魏茨曼解釋說:「但我們的猶太精神與錫安主義是可以彼此相通的。」一八七八年,巴勒斯坦猶太人在沿海地區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希望之門),不過此時就連羅特希爾德家族——在法國的艾德蒙男爵主持下——也開始出資讓俄國移民建立農業聚落,例如里雄勒錫安(Richon-le-Zion),先至錫安者,總計捐助了六百六十萬英鎊的鉅額捐款。與蒙提費歐里一樣,他企圖買下耶路撒冷城牆。一八八七年,穆夫提穆斯塔法.侯賽尼(Mustafa al-Husseini)同意這項交易,但這後這項交易卻未能實現。當羅特希爾德於一八九七年再次嘗試時,卻遭到侯賽尼.謝克.哈拉姆(Husseini Sheikh al-Haram)回絕。
赫茨爾信仰錫安主義,但他的錫安主義並非由下而上、由移民建立起來,而是由上而下、由皇帝批准與財閥資助而成。羅特希爾德家族與蒙提費歐里家族起初鄙視錫安主義,但首屆錫安主義會議卻因法蘭西斯.蒙提費歐里爵士(Sir Francis Montefiore)的參與而增色不少。法蘭西斯是摩西的姪子,是一名「相當愚蠢的英國紳士」,他在「瑞士夏天的高溫下仍帶著白手套,因為他想到自己可能要跟很多人握手」。儘管如此,赫茨爾仍需要一名有力人士來幫他向蘇丹說項。他認為他的猶太國家必須是德語系國家——因此他轉而從現代君主國中尋找學習的範本,而他的目標顯然是德國皇帝。
儘管赫茨爾未能成功說服任何皇帝與蘇丹,但他的錫安主義卻激勵了俄羅斯境內受迫害的猶太人,特別是普翁斯克(P?ońsk)一個富裕律師家庭的男孩。十一歲的戴維.格林(David Grün)認為赫茨爾是彌賽亞,他能領導猶太人回到以色列。
《紐約時報》報導說,群眾「穿上假日的服裝,城市居民纏著白頭巾,華麗條紋上衣」,土耳其軍官的妻子穿著美麗絲質的米拉耶(milayes),富裕的農民穿著火紅飄逸的長袍,至於貝都因人則騎在駿馬上,「穿著簡陋的紅靴,上衣圍著一條皮腰帶,佩戴著一大堆小型武器」,頭上纏著阿拉伯頭巾。謝克手持長矛,矛尖上綁了一團鴕鳥羽毛。
在猶太凱旋門,年過九旬、滿臉鬍鬚的塞法迪大拉比,身穿土耳其長袍,頭纏藍頭巾,而另一名阿什肯那吉拉比則向威廉獻上《摩西五經》複本。而威廉也受到耶路撒冷市長雅辛.哈立迪(Yawww•hetubook•com•comsin al-Khalidi)的歡迎,後者披著莊嚴的紫披風,纏著金色滾邊的頭巾。威廉在大衛塔下馬,他與皇后從這裡走進城內,為了預防無政府主義者行刺(最近曾發生奧地利的伊莉莎白皇后遇刺事件),於是淨空了民眾。宗主教穿上最華麗的服飾,戴上象徵教會權力的配件,引導威廉走進聖墓教堂。當德皇循耶穌昔日的腳步前行時,他的內心「澎湃不已」。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德皇騎著白馬,從雅法門旁一個特別鑿開的缺口進入耶路撒冷。
新興的歐洲民族主義,使猶太人這個超國界的世界主義民族遭受各個種族的敵視——然而在此同時,民族主義加上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自由,也激勵了猶太人。不僅波騰金公爵、拿破崙皇帝與美國總統亞當斯深信猶太人應回到耶路撒冷,連波蘭與義大利民族主義者,以及英美的基督教錫安主義者也這麼想。不過,錫安主義的先驅主要是正統的猶太教拉比,他們把回歸耶路撒冷與彌賽亞連繫在一起。一八三六年,普魯士的阿什肯那吉拉比卡利舍爾(Zvi Hirsch Kalischer)向羅特希爾德與蒙提費歐里家族尋求資金,援助建立猶太國,他日後完成一部作品《追尋錫安》(Seeking Zion)。在大馬士革「血誹謗」事件結束後,塞拉耶佛的塞法迪拉比阿爾切萊(Yehuda Hai Alelai)呼籲伊斯蘭世界的猶太人選出自己的領袖,買下巴勒斯坦的土地。一八六二年,馬克斯的同志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羅馬與耶路撒冷;最後的民族問題》(Rome and Jerusalem : The Last National Question)中,預言民族主義將會導致反猶太的種族主義,他並且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社會主義猶太社會的構想。然而真正具決定性的,卻是俄國屠殺猶太人。
德皇威廉不可能支持猶太人建國。當他聽聞猶太人移居阿根廷時,他說:「要是我們也讓德國人移居那裡就好了。」而當他得知赫茨爾的錫安主義時,他寫道:「我很高興這些討厭的猶太人要搬去巴勒斯坦。希望他們越快越好!」雖然威廉定期與德國的猶太實業家聚會,而且也是猶太船主巴林(Albert Ballin)的朋友,然而他打從心裡討厭猶太人,經常痛罵猶太資本主義是有毒的禍害。猶太人是「我的帝國的寄生蟲」,他認為猶太人正在「扭曲與腐化」德國。過了幾年,當威廉遭到罷黜之後,他提出以瓦斯來大規模滅絕猶太人的計畫。然而赫茨爾卻認為「這名反猶太人人士會成為我們最可靠的朋友」。
德皇離開耶路撒冷前往大馬士革,並且在當地宣稱自己是伊斯蘭的保護者,打算為薩拉丁修建一座新墳。此時,赫茨爾則是從三名身穿土耳其長袍的健壯猶太挑夫看到未來:「如果我們能讓三十萬名跟他們一樣的猶太人來此地定居,整個以色列就是我們的。」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德皇與皇后搭乘御用列車,隨員包括外交大臣、二十名廷臣、兩名醫生,以及八十名侍女、僕役與侍衛。為了讓全世界注意他這次旅行,威廉特別自己設計了一套白灰色的軍服,以及等身的十字軍風格白色罩紗。十月十三日,赫茨爾與四名錫安主義同志搭乘東方快車從維也納出發,隨身帶著需要的服裝,包括白色領帶與燕尾服,以及防暑帽、狩獵裝。
十一月二日,赫茨爾終於得到皇帝召喚——這五名錫安主義者異常緊張,其中一人甚至提議服用鎮靜劑。他們穿著適當的服裝、白領帶、燕尾服與禮帽,來到大馬士革門北方的德皇營地。這是奢華的湯瑪斯.庫克(Thomas Coo
https://www.hetubook.com•comk)村,擁有兩百三十個營帳,用一百二十輛馬車運送,一千三百匹馬馱運,一百名馬伕照管,動用六百名駕駛,十二名廚子與六十名侍者,四周則有鄂圖曼士兵保護。觀光大亨約翰.庫克說,這是「自十字軍以來,前來耶路撒冷的人數最龐大的一次。我們幾乎蒐羅了這附近所有的馬匹、馬車與糧食。」英國畫報《笨拙》(Punch)嘲笑威廉是「庫克的十字軍」。一八九七年八月,赫茨爾在巴塞爾(Basle)主持第一次錫安主義會議,之後他在日記裡誇耀說:「朕即國家。在巴塞爾,我建立了猶太國。如果我在今日大聲說出這種話,我將換來眾人的笑聲。或許五年後,甚至於五十年後,每個人才會知道我所言不假。」他們確實發現赫茨爾是來真的,而且只花了五年的時間。赫茨爾成為新類型的政治人物與政論家,利用新鋪設好的歐洲鐵路周遊列國,遊說君主、大臣與新聞大亨。他馬不停蹄地四處奔走,加重了他原有的心臟痼疾,嚴重的話,可能隨時奪走他的性命。
對赫茨爾來說,這也是好消息:「反猶太的呼聲在各地不斷高漲,猶太人在驚恐中不斷地尋找保護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會尋求蘇丹協助。」赫茨爾狂喜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赫茨爾
威廉二世計畫進行一趟東方之旅,除了會晤蘇丹,也準備到耶路撒冷為他父親獲贈的一塊土地上蓋的教堂進行獻堂儀式,這座教堂就緊鄰在聖墓教堂旁邊。不過威廉還有別的計畫:他對於自己與蘇丹的會談結果感到自豪,而且認為自己是一名前往聖地的新教朝聖者。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由德國來保護鄂圖曼人,提升他的新德國地位與削弱英國的影響力。
德皇誇示著他的白色軍服,等身的金絲罩紗從頭盔尖端的金鷹垂了下來,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他身旁護衛、戴著鋼盔、身形高大的普魯士輕騎兵隊,他們手持十字軍風格的旗幟,還有蘇丹長矛輕騎兵,身穿紅色背心、藍色馬褲,頭上纏著綠色頭巾,手中持著長矛。皇后穿著有圖案的絲質衣裳,戴著飾帶與草帽,乘坐馬車跟在皇帝後面,身旁坐著兩名侍女。
赫茨爾需要新的支持者:他提議在賽普勒斯或西奈的阿里什(屬於英屬埃及的一部分)建立猶太國家,這兩個地方都接近巴勒斯坦。一九○三年,第一任羅特希爾德勳爵那提(Natty)終於傾向於錫安主義,他引薦赫茨爾與殖民地大臣約瑟夫.張伯倫見面,張伯倫排除了賽普勒斯的可能性,但同意考慮阿里什。赫茨爾委任一名律師草擬猶太人定居的特許章程。這名律師是四十歲的自由黨政治人物勞合.喬治,他將做出自薩拉丁以來,影響耶路撒命運最大的決定。令赫茨爾失望的是,這項請求被回絕了。張伯倫與首相貝爾福(Arthur Balfour)提出另一個地區——他們提供烏干達或肯亞的一部分做為猶太人立國之地。沒有選擇的赫茨爾只好暫時應允。
赫茨爾看到皇帝穿著「灰色殖民地軍服,戴有罩紗的頭盔,褐色手套,手上拿著馬鞭(這真是夠奇怪的了)」。這名錫安主義者趨前,「停下腳步,然後鞠躬。威廉殷勤地伸出手來」,然後對他說:「這片土地需要水源與遮蔭。這裡充滿了機會。你的想法是可行的。」當赫茨爾解釋供應飲用水雖然可行、但非常昂貴時,皇帝回答:「關於這一點,你們有的是錢,你們比我們都要來得富有。」赫茨爾提議建設一個現代的耶路撒冷,但皇帝卻終止了這場談話,而且「不置可否」。
諷刺的是,德皇與赫茨爾都不喜歡耶路撒冷:「一處陰鬱不毛的石頭堆,」威廉寫道,「猶太人聚居的現代市郊讓這一切顯得更為糟糕。這六萬名猶太人,油膩而污穢、阿諛而卑鄙、不事生產,只想著占鄰居便宜——他們是一群夏洛克。(譯註: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放貸者。)」威廉寫信給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到現在的他比過去更厭惡基督徒「徒務外表的裝飾」——「離開聖城時,我覺得自己在穆斯林面前抬不起頭來」。赫茨爾跟德皇的想法幾乎一樣:「日後當我回想起來,喔,耶路撒冷,我將不會感到喜悅。在臭氣薰天的巷弄裡,陳腐沉澱了兩千年的不人性、不寬容與卑鄙無恥。」他認為,西牆到處都是「骯髒、可悲、無孔不入的乞丐」。和*圖*書
「我要去覲見德皇,告訴他,『讓我們的人民離開』,」赫茨爾說道,他決心以「這個偉大、強盛、道德、治理完善、組織井井有條的德國做為猶太國的模範。透過錫安主義,猶太人將會再度喜愛德國。」
儘管如此,威廉還是將赫茨爾的提案轉告阿布杜爾-哈米德。蘇丹馬上就拒絕了,他對女兒說:「猶太人大可把他們的錢省下來。當我的帝國分裂時,或許他們可以不花一文錢得到巴勒斯坦。但他們得先把我的屍體大卸八塊才行。」在此同時,對伊斯蘭的活力感到讚嘆的威廉,也對赫茨爾失去了興趣。
一九○三年四月,在沙皇內政大臣維雅切斯拉夫.馮.普勒維(viacheslav von Plehve)的支持下,在基希內夫(Kishinev)對猶太人進行了無節制的屠殺,這項行動擴展到整個俄國。赫茨爾在驚慌之下前往聖彼得堡與極端反猶太主義者普勒維協商,然而在無從連繫德皇與蘇丹之下,他只能在聖地外尋找猶太人臨時的棲身之地。
威廉:我的帝國的寄生蟲
赫茨爾斷言,猶太人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才可能得到安全。起初,兼具實用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傾向的赫茨爾,夢想建立一個德意志貴族共和國,一個由元老院統治的猶太威尼斯,由羅特希爾德家族成員擔任統領,赫茨爾自己則擔任議長。赫茨爾構想的國家是世俗的:高級教士「穿著華麗的祭袍」:騎兵穿著銀色的胸甲;猶太市民則在現代的耶路撒冷鬥蟋蟀與打網球。羅特希爾德家起初對於猶太國的構想感到懷疑,他們反對赫茨爾的提案,儘
https://www.hetubook•com•com管如此,這些初具雛型的念頭不久就發展為成熟而可行的方案。一八九六年二月,赫茨爾在《猶太國》裡提到:「巴勒斯坦是我們永遠不會忘懷的歷史故鄉。馬加比家族將會再起。我們最終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像自由人一樣生活,可以在自己的故鄉安詳地死去。」
赫茨爾感到印象深刻。這位霍亨索倫王室權力的化身,有著「像大海一樣湛藍的眼睛,細緻嚴肅的臉孔,坦率、和藹但卻大膽的態度」,但事實並非如此。威廉無疑相當聰明,也擁有充足的知識與精力,然而他卻容易不安與前後不一,有時嚴重到連歐伊倫堡伯爵都懷疑他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在剝奪了俾斯麥首相職位之後,威廉獨攬大權,但他沒有能力提出一貫的政策。他的外交方針是一場災難;他寫給大臣的便箋慘不忍睹,大臣們為了不讓別人窺見,只好將這些文件鎖進保險箱裡;他在公開演說屢屢發出驚人之語,例如他鼓動軍隊對德國工人開槍,或者要像屠殺匈人一樣地對付敵人,這些話讓聽者感到困窘不已。早在一八九八年,威廉已經被人認為是半個丑角,半個戰爭販子。
然而耶路撒冷已經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聚居地:在四萬五千三百名居民中,有兩萬八千名是猶太人,這個數字令阿拉伯領導人感到憂心。「誰能與猶太人爭奪巴勒斯坦的權利呢?」老尤蘇夫.哈立迪於一八九九年對他的朋友法國大拉比撒督.卡恩(Zadok Kahn)說。「上帝知道,歷史上它的確是你們的國家」,但「現實的殘酷力量」使「巴勒斯坦現在屬於鄂圖曼帝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裡住的不只是以色列人。」這封信已然預示了巴勒斯坦建國的觀念——哈立迪是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鄂圖曼人,而最終是世界的公民——而且提出了否認猶太人對錫安的主張的必要,他已經看出猶太人的回歸,古老而具正當性,將與同樣古老而具正當性的阿拉伯人起衝突。
赫茨爾必須滲透到德皇的宮廷中。首先,他設法見到皇帝的叔叔,即深具影響力的巴登大公弗里德里希,大公對於尋找約櫃的計畫頗有興趣。他寫信給姪兒威廉,威廉於是要求歐伊倫堡伯爵菲力普向他報告錫安主義計畫。歐伊倫堡伯爵是德皇最好的朋友,也是派駐維也納的大使與政治智囊。伯爵深受赫茨爾計畫的吸引,相信德國可以利用錫安主義來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德皇也認為「閃族的活力、創意與效率,要比腸枯思竭的基督徒更能找出有價值的目標」。威廉與當時絕大多數的統治階級一樣,相信猶太人擁有主導世界運轉的神秘力量:
赫茨爾從擠滿德國軍官的飯店裡看著皇帝的行列。皇帝認為耶路撒冷是個絕佳的舞臺,可以用來宣揚他新打造的帝國,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吃他這一套。俄國皇太后就認為德皇的做法「荒謬得令人作嘔!」德皇是第一位任命官方照相師在國是訪問時進行拍攝的國家領袖。十字軍的軍服與大批照相師顯示了歐伊倫堡伯爵曾經說過德皇的「兩種全然不同的特質——具有騎士風格,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黃金時代,以及現代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