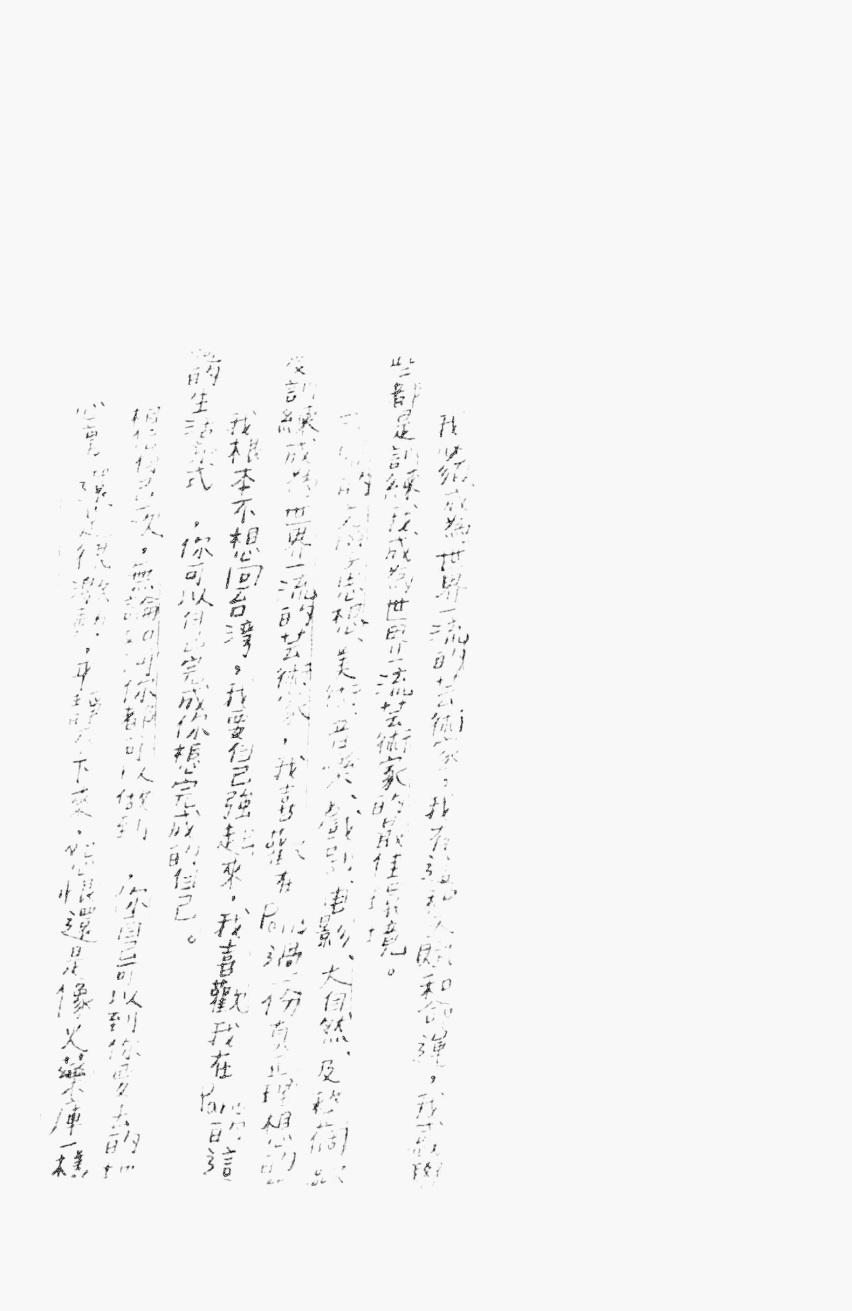第十四書
——Angelopoulos《重建》(Reconstitution)
是的,她是個有德行的女人,我無法向任何人,也無法找到任何方式,表達絮的具體形象,表達她在我心中雕下的真善美……我想雕刻家在刻他心中的永恆容顏時,是必須在時間中找出如大理石般堅硬的凝結點,是必須在變化的流沙裡鑿出永恆的意志,是如此的吧?
九四年六月,絮搭飛機到巴黎來,與我一起實現長久以來我們對愛情婚姻的夢想與理想,直至九五年二月,我送她回台灣,這之間的婚姻生活一日敗過一日……可說來到我眼前的已不是一個我所認識的她,當她踏上法國實踐她對我最後諾言的第一天起,她已自她身上離開,我已失去一個百分之百愛我的絮。我常說她來巴黎不是來愛我的,是來折磨我的。她努力地試圖善待我,卻只是給出更多不愛、冷漠與傷害……關係急遽和-圖-書惡化,八月,她開始不忠於我,我陷入長期的瘋狂狀態,一點一點地自我毀滅,自我崩潰,之間兩次企圖死去,企圖從生命中最血腥最恐怖的內在夢魘裡逃脫……而她變得愈來愈冷漠、可怕、更嚴重的不忠傾向……最後我完全無法挽救自己地傷害她……內部深處被戳傷太重,彷彿在面對一名最狠辣的仇敵……她也幾乎被我毀滅,恐懼我至無以復加……
想及割耳後頭包繃帶的梵谷畫像,想及太宰治所深愛的「頭包白色繃帶的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
(除了不誠實之外,我們別無所懼。)
九五年三月我回到法國繼續學業,為了要我離開台灣,她答應我要共同修復起我們的愛情,給我們希望,彼此再各自治癒,她會待在那裡等我再等我……我太可憐又太脆弱,不敢也不曾去想她已經不再是那個令我信任、尊敬、有德行的她了,因為https://m.hetubook•com.com那個「她」已被我親手摧毀了……〔是的,是被我摧毀的,遠在她來法國前的一個月內,我已將她内部所向我展開的美麗摧毀,當我明白她並非真正願意為我的生命負責,並非真正願意來法國(而她自己並不願知道這一切)時,我在電話中將她及她的愛一股腦地丟擲回去,丟擲在地,我決心獨自在法國走下去,不要再等她,我絕望地關在小公寓裡,拔去電話,拒絕她又拒絕她……那時她心已碎,愛我之魂魄已飛去……一個月内匆匆成行,趕著來巴黎挽回我,挽回這關係的她,唉,是一個連她也不知道是誰的她,是一個根本不想離開家的她啊!]
一九九二年九月遇見絮,到十二月搭機前往法國,是邂逅,也是蜜月。九二年年底,我先在小城裡學法文,隔年九月轉上巴黎念研究所,直至九三年六月,是盟誓期,完美的愛情關係,絮堅定如石地支撐著我朦朦朧朧的留學理想,閃爍著光芒照耀
和*圖*書我孤獨的自我追尋之旅程。三百多封書信,使我愛情的性靈燦爛地燃燒。此情此恩啊,我怎能蒙上眼睛騙自己說,還有更美麗的人在等我,我怎能關掉心裡的聲音而告訴自己說我還可以更愛另一個人,我怎麼可以佯裝沒看見我的生命所被她剪裁出來的形式,而說我還能再歸屬於另一個人,說「愛情」不是這樣,是別樣,是在他方……
五月三十一日
無意識地狂號嘶叫,無意識地撞著電話亭的玻璃或鐵架,無意識無痛感地血在頭上橫流又橫流……我對著話筒裡的她吼著:(我今天就要死去!):警車停在亭外,四名警察要帶我走,我堅持要講完電話……混亂中聽見絮哭著說立刻就離開別人的家,回家會馬上打電話給我,會儘快到巴黎來和我談清楚……然而,這每一句話都是謊話,每一句謊話又都更深地危害到我生命的存在……謊話之上唯有更多的謊話……兩名警察將我拖出電話亭,我掙扎不從,和-圖-書想再拿回話筒……我被拖進法國的警局,大腦彷彿已經昏厥過去,癱在地上只感覺有許多雙腳在我身上踢打,劇痛卻也麻木……忘記自己是怎麼站好,怎麼踏出警局門口,怎麼走路回家,我已忘記,只留著一些深刻的精神痕跡,我想精神深處我在驅使自己要有尊嚴地走回家,要回家坐在電話機旁等絮的電話……我回到家了,全身不知名的疼痛腫脹,五臟六腑恍若碎裂,不間斷地嘔吐……那個凌晨,黑暗中我坐在客廳的電話機旁,耳邊轟轟作響:「你真的要死了!」
(Un homme vit avec une femme infidele. Il la tue ou elle le tue. On ne peut pas y couper.)
直到我因她而死的最後一天,我都還信仰著她的德行,她的誠信,她的言行一致……三月十三日,離開台灣的第十天,她睡在別人家裡,別人床上……在公共電話亭裡,我瞬間https://www•hetubook.com.com死去,經驗到半年裡我内在被她的不忠所累積的暴力及死亡的全部意涵。是的,我死去……死亡.發生.死亡.死亡.發生。
一個人和一個不忠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殺掉這個(女)人,或是這個(女)人殺掉他,這是無法避免的事。
嘴巴代表真誠。鼻子代表寬厚。兩道眉毛代表正直。額頭代表德行。眼睛代表愛人的能力……
我細細撫觸她的臉,她的五官,喃喃說出她在我心中的美。是的,這就是她。當鳥兒飛過浮雲,掠上我心頭的就是這一張心像;當雙眼凝視水面,水波中漂現的就是這幅幻影。那是我在飛翔的雲間看到的?還是我從我心裡看到的?她是幻影嗎?還是水的流動原就是幻影?